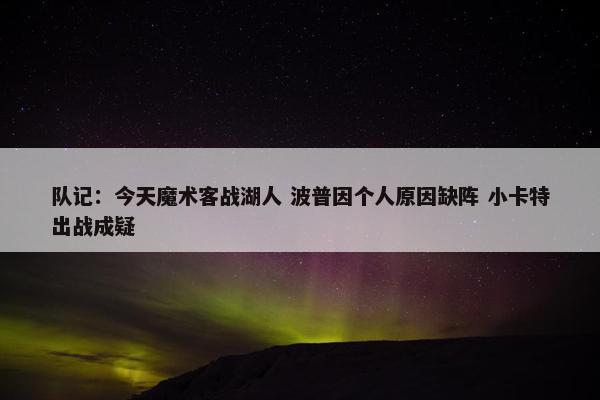南桥 _ 打不过就加入?说说人工智能浪潮下翻译的从业危机
明侦值得反复刷的案件
指挥家余隆、上海交响乐团、纽约爱乐乐团合作了一部清唱剧《上海!上海!》(Émigré),讲述1930年代上海犹太难民的事,由于美国反移民和巴以冲突,此剧找对了风口,在西方产生了重大反响。
人工智能正在改变各行各业。但未必是哪个领域声量最大,改变就最大。人们惊呼Sora将改变*甚至影视行业的时候,可能疏忽了改变最大的还是语言翻译。人工智能对*的冲击,暂时还没那么大,好莱坞和横店都还可以活一阵子。但无论是ChatGPT、Gemini、CoPilot,还是“文心一言”,所有平台都始于“大语言模型”。语言才是这些人工智能的主场和大本营。人工智能对于翻译的改变,是立竿见影的。它不仅冲击了过去一度庞大的翻译产业,也改变了高校的专业设置图景。外语专业的衰败,早已开始,但可能还没有探底。人工智能带来的恐慌,远未消停。
毋庸置疑,人工智能翻译的质量会越来越好。神经机器翻译 (NMT) 系统,使用深度学习算法,分析和理解翻译的上下文,从而提高翻译的准确性和流畅性;自然语言处理 (NLP) 技术,可以帮助人工智能翻译工具理解语言的细微差别,这对提高翻译质量至关重要;机器学习算法,可以分析大量数据,找出可用于提高翻译准确性和流畅性的模式,提高翻译的质量;云端翻译的工作模式,会有助于搜索引擎的“爬虫”在无边无际的互联网翻山越岭,迅速查到资料,一解过去查资料的繁复辛劳。所有这一切,都会让人工智能辅助之下的翻译,质量越来越好。换言之,低端翻译会无悬念无后路地被替代。这就别存什么侥幸了,早死心,早超生。
除了“谁”在翻译(是人工还是人工智能)这个问题之外,翻什么和不翻什么,也值得思索。一些材料在世界各地“旅游”,过去是翻译“带队”。假如这些材料走到哪里,哪里随时都有“地陪”,还需要一个人去全程陪同吗?有一些文献被正式翻译的可能性会下降。倘若此类文献在网上即可以借助DeepL之类插件,随时可以点击进行“云翻译”,那么放在网上就可以,人们在需要的时候随时一点,出版者何必走翻译和质量控制的流程,而读者又何必等待他人翻译好了来投喂?云计算已经进入寻常百姓家,我们已经习惯了需要材料的时候即时上网搜索,而不是预先囤积起来占地方。现在人们面对的问题,不是知识的匮乏,而是过剩。有了云计算打底,这种随到随得、及时领取(just in time)的翻译模式,会取代专人对整个文本的翻译、编辑和出版。
这种及时领取,也是一种“刚刚好即可”(just enough)的知识消费心态。这种消费心态是被读图和*时代缩短的注意力培育出来的,让人有些无奈。但话说回来:很多文本(如学术文献、技术文献、法律文件、医疗文献),阅读者只需要泛读和速读,理解八九成也就够了。这种内容的消费,会和一个人现有的知识结构结合,产生化学反应。有时候我们的内容消费,往往不是为了消费而消费,而是有其他目的,比如了解前沿新知,这需要大量浏览,量变到质变地产生见识或者方案,需要进一步了解的时候再去细看不迟。学术文献分析,很多时候,顶尖学者也只是看看摘要,看有无有价值的观点、方法、结论,有需要的时候才去细看。不过,涉及文学翻译,那10%的差距,或许正是文字的精华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常有人说诗歌不可译的一个原因:译作的受众或许得到了意思,失去了诗意。从这方面看,最了解诗人的还是人,最好是诗人,而不是人工智能。
人工智能也给过去在翻译领域求生的人,创造了新的机会。人工智能翻译工具将能够帮助人们检索不同语言的信息,打破语言壁垒,让每个人都能获得所需的信息。换言之,翻译有可能会融入到写作过程当中。这会带来一些伦理道德上的挑战,例如一些抄袭,会变得更难以觉察。你只有自己用多了,才能火眼金睛,一眼看出ChatGPT的痕迹。像李一舟这样,利用这种人工智能鸿沟造成的信息差,“倒卖”外部知识的内容掮客,可以趁机发家。目前法律的完善,还跟不上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。如果法律上没有做错,对这种人工智能时代“投机倒把”的精明人,他人也无权过度谴责。人工智能也因此在语言的沟沟坎坎之间,滋生出大量的机会——这机会远远不限于翻译领域。如果你不及时捕捉这种机遇,你会成为这种改变中的看客。
例如,它会做大蛋糕,使得翻译量产化。人们往往把目光纠结在人工智能翻译的“质”上,亦即准确性和人工相比究竟怎样,这个译本好还是那个译本好?很多古代的传统经典,如四大名著和唐诗宋词,基本靠杨宪益、戴乃迭或是许渊冲这些大家,他们一辈子出产那么多,已经耗尽心血。时下翻译中缺乏的是选材上的创造性思维。同样作品(尤其是公版)被大量重译,一部好作品被翻译了热销,其他人就跟着去炒冷饭,同类译本多如牛毛,恶化了竞争。为了让自己的译作出头,有的人不惜攻击他人,恶化了生态。这完全是翻译界的内卷,造成的是严重的资源浪费,有点像经济领域的重复建设。
而大量优秀作品藏在深山,从来没有人翻译过。出色的译者人数少,“生产周期”长,难以大批量翻译。这些可以视作“长尾”的作品,现在能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,更多更快地被译介为其他语言。一些中国过去的作品翻译,也有助于改变世界和中国的关系。很多故事未被讲述,道理未被理解,造成大家思维的差异被忽略。一旦讲述,可能影响深远。例如指挥家余隆、上海交响乐团、纽约爱乐乐团合作了一部清唱剧《上海!上海!》(Émigré),讲述1930年代上海犹太难民的事,由于美国反移民和巴以冲突,此剧找对了风口,在西方产生了重大反响。而类似的文字作品,一旦翻译出来,也会有类似效果。
同样,外文作品中的优质作品,引进过来可能会改变一个人、一个行业、一个学科的命运。这些作品汗牛充栋,是绝大部分没有被翻译成中文的。人工智能可以革命性地提高翻译速度,提高人工效率。不要说文学经典,就是一些宗教文献,被完整翻译的都还很少。过去玄奘翻译佛经,由于人力不足,很多地方是囫囵吞枣的,所以才有“般若波罗蜜”之类在汉语环境下人们不知所云的音译做法。而更多的衍生文件,包括注释、评论,则更是淹没在故纸堆中。人工智能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,人类终于有能力大规模去发现、发掘新的重要典籍和文献了。
既然有待翻译的材料更多了,人工智能会成为改变翻译选择的触媒,翻译行业自身的机会在哪里?人们讨论得更多的是人工被替代的问题。如上所说,低端翻译被替代是没有悬念的,但是需要更多精确性和美感的翻译仍不可少——他们是面临机会的一群人。面对“人工”和“智能”的相互关系,“替代”是一种可能。“打不过就加入”也滋生了诸多可能,包括“辅助”和协作。从八分人工两分智能,到两分人工八分智能,还有其他比例的组合方式,都会出现。
翻译工种会出现内在的核变。如英伟达的黄仁勋所言,未来会使用人工智能的会取代不会使用人工智能的,这或许是替代论最为到位的解释。我从很早做翻译的时候,就开始使用机器辅助。我有几本译作,整个翻译过程都是在Google Translate Toolkit上完成的。那时候机器翻译的质量有限,我主要使用平台,一句句对应,更好地集中注意力,排除外在干扰,避免错漏,翻译工作自身被改善的倒是很少。在计算机辅助翻译的时候,机器可以帮助术语的统一,提供查询的便利,而人工则是翻译的主体,这时机器和人工的投入可以说是二八开:机器提供20%的帮助,但是80%还是人在做。一些难度大的作品,机器仅提供术语、查询等方面的辅助。
人工智能则颠覆了人工和智能的合作方式,智能和人工之间的分工,变成了五五开,甚至七三开、八二开了。人工的主要作用变成了对人工智能翻译的编辑和修理。人工的作用,还可体现在工作流程的变化上,比如先用人工智能粗扫一遍,然后人工加工,最后再让机器整理译作。整个过程更具有循环往复、螺旋式改进的特征。机器和人工不再是协助和被协助的关系,而是一种团队合作的关系。善于开展这种合作的人,能生产出更有质量的译作。这种协作,对人工的要求更高一些。人工智能的翻译质量通常相当不错。你若段位尚在其下,则无法识别问题,将其产出优化。语言水平高、更有创意的人,可以向人工智能提供更好的“投喂”,生成更好的作品。这种情形下,人工和智能会相得益彰,珠联璧合,是所谓的“better together” 。
我有时候甚至觉得,人工智能对于翻译的需求来说,步伐还是慢了一些,没有更为革命性地解放人工。目前,能够贴近译者需要的人工智能化翻译平台,还是少了一些。大语言模型集思广益,能够实现更为广义的学习,而对于翻译者的个体化需求,追踪得还不够快。例如,你在翻译一本著作,引述过多,前后的引文统一起来,仍难如人意。塔多斯之类平台,还有一点门槛和壁垒,并没有像谷歌翻译那样可以无所不在。但愿未来人工智能翻译工具还可以学习并适应个别作者的写作风格,并有办法对已有翻译进行存储,智能地对同一个人未来的翻译进行协调整合。目前,在具体词汇上可以做到这一点,但是在句子和段落上,还难以一以贯之地调整措辞和风格。这种个性化翻译,也可以表现在作者风格的匹配上,比如在文学翻译上,难的是作者风格的整体对应。如哈珀·李在《杀死一只知更鸟》中用的是阿拉巴马州的方言。托尼·莫里森常用肯塔基的黑人方言。马克·吐温和福克纳则多使用密西西比方言。到目前为止,大部分译作在这种方言风格的整体转换上都是有欠缺的。人工智能可以提供激动人心的可能性,比如译作可以在对人工智能的二次投喂中,产生出新的、统一的风格。
总而言之,在人工智能摧枯拉朽地改变下,翻译行业未来有多种可能。笼统地说,一部分人会沦为看客,而另一部分人会成为知识的掮客。一些人的饭碗被砸掉,一些新的饭碗会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。目前我对人工智能的潜力是叹服的,更多的时候,在人工智能面前,或许“打不过就加入”也是不错的选择。当然,更好的办法是驾驭它。技术从来就是好奴仆、坏主人。
南桥
责编 刘小磊